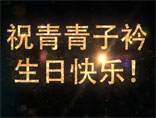却是小白。没想到他却一路闻着我的气息,跟到这里来了。
我把他洗干净,黑毛变回白色,想来受了不少苦,瘦的不成样子,调养了半个月,才终于又活泼乱跳起来。我采药带着它,在山上见了几回猎狗,竟然自己也去捕猎,第一次带回了一嘴的鸟毛,鸟却没见着,第二次带回了一只死兔子,我查看兔子伤口,不是在脖子上,却是在头上,我猜是不小心撞到大树被小白捡回来了。捡了便宜货的小白很兴奋,第二日天还没亮就精神抖擞的往山上冲,半夜,拖了个受伤的男人回来。
我蹲下身教育他,不能吃的东西不要乱拖回家,它似懂非懂点点头。
我查看了下地上类似尸体的东西,被小白拖回来的男人受了重伤,不过一息尚存,居然还没有死。衣服已经被染得全是血渍,棉质,非丝非绸,看来并不是大富大贵之家,身上大小伤口几十处,右手骨头和肋骨骨断了几根,下手这么狠毒,想来是遭了仇家之手,近来江湖纷争扰乱,应是江湖人士。
我按照中原的诊断方法把了他的脉络,发现致命的伤却不在身上那些皮肉翻飞的伤口上,而是身体里的毒。嘴唇发黑,经络涣散,瞳孔放大,手臂上有细小的梅花形的黑斑,这些都是岁忆之毒的症状,婆婆曾告诉我解此毒的法子,甚是艰难,连步骤都记不全了,只隐约还在脑海里留下婆婆的声音:“那儿的梅花快要开了吧,便叫它岁忆好了。”
我并不是中原的医者,不需要常怀医者父母之心,江湖厮杀,我从慕容家出来,便不愿再听分毫,况此人身染岁忆之毒,我并不想经手。
“小白,哪儿拖来的拖回哪儿去。”我起身,向里屋走去。
死生有命,被救未尝不是痛苦,死亡未尝不是解脱。
方转身,裤脚却被扯住,听得小白呜呜的哀求,我蹲下摸摸它头,它很乖的伸过头来蹭蹭,尾巴不停晃,眼睛亮晶晶的望着我。
小白啊,这个便宜货吃不得,下次还是捡兔子好。我耐心教导。
地上的尸体却沉沉呻吟了声,动了动。衣服上一块破布浸足了血,摇摇晃晃剥落下来,露出心口一块肌肤,一个狭长的伤口深深的延进去,擦过心脏,几乎致命。我心一紧,呼吸急促起来,这个伤口的形状再熟悉不过,未曾想会出现在此。
当初斩断我眼前毒蛇的一剑,剑尖斜圆,上剑刃稍厚,下剑刃稍薄,名为省身。
这剑,也是我的伤口。
慕容景轩,既然是你要杀的人,我怎能让他死?就算逆天,我也会将他救活。
指尖刺了血出来,我的血和他的竟然相合,省却许多麻烦。于是让小白叼了鹅,取了羽翅上最剔透的细管换血,我体质稍弱,为免反噬,断断续续换了七日,采齐了药,同玛尼石一起熬煮内服,兼之敷伤药,接骨包扎。第七日,他手臂上的梅花斑开始慢慢消去,伤口也开始愈合,生死之关,便跨过去了。
却还是没醒,我每日守着,用竹管将讨来的牛乳灌入口内吊着一口命,兼之擦拭伤口,更换药草。有时自己想想也很好笑,明明以为已经不在乎的人和事,原来早已经像蔓藤一样爬满心口,一个浅浅的缝隙便喷薄出来,让人不知所措。
也罢,算我任性一回。
换着药,在那人左手大拇指处翻检到一个青铜的扳指,颜色古旧而有些斑驳,上面有隐约的图案,仔细辨认可以看出是一只展翅的鹰,迎面扑来的形状。勾画的线条只是寥寥几笔,很粗犷,却极有神韵,右下角却有个分明的“汉”字。我微微有些出神,那个凶狠的鹰像,仿佛曾在梦里见过。
这人,究竟是谁?
扒开头发看了看那人的脸,轮廓很好看,线条分明,睫毛长长的压着,像沉睡的蝴蝶。眉峰却似剑,凛冽锐利的斜飞,英气一下子就衬出来。嘴唇薄薄的抿着,呼吸长一声短一声。婆婆曾说薄嘴唇的男人都刻薄得像刀子,却最是让人爱恨交织,说的就是这种相貌吧。
不得不说,那张脸很耐看,看一眼有一眼的味道,连侧脸刚愈合的伤疤也是很好看的,天知道把这张脸扔出去能祸害多少女子。
“没有一万也有八千吧。”许久之后我漫不经心提到此想时,某人挑眉一笑,如是回答。
初春的阳光总是很暖,整个山里都弥漫着清香,草芽树叶刷刷的冒出来,树梢上也开始出现幼鸟的啾啾声。婆婆说,所有的东西在春天都要长得快一些,当然这也包括床上那个尸体的伤口。
伤口愈合得很好,在小白捡回便宜货的第九天,他终于睁开眼。
我和小白照例守在床头,我方半寐,小白见他醒了,高兴的咧嘴扑了上去大大舔了一圈,又回过头来把我舔醒。他的眼睛慢慢打开,从小白的血盆大口缓缓飘过来,看见我,张开嘴唇似要努力说话。
我撇了他一眼,探探呼吸,活的。于是径直起身,回到里屋睡觉。走到门廊处顿了一顿,好心说了句:“水在床头。”
再走两步,听见竹床吱呀响了一声,应该是在试探哪儿的骨头还能动。于是我再好心提点:“左手没断。”床再吱呀一声,补一句:“水在右边床头。”
哐叽听见下巴磕在枕头上的闷哼声。我欢快跳上床,盖好被,安稳睡觉。
片刻,小白也欢快摇着尾巴跑到我床头,蜷好,睡觉。我迷迷糊糊摸了摸它脑袋,嘴边有点湿,想来是把水抢了,我再迷迷糊糊的夸了声,真乖,然后睡着了。
直到第二天的太阳把我晒起来。